刊载于2012年5月三联《爱乐》
第一部分 西贝柳斯所生活着的芬兰
关于让.西贝柳斯的资料和文章,是笔者一直留心着的,现在看来,这位芬兰作曲家的魅力似乎已经延伸到了音乐之外的范畴,凡提起芬兰,必会捎带提到西贝柳斯;凡说到西贝柳斯,必会议论一番芬兰的近况。最近。与一席朋友谈起芬兰的时候,他们脑海中对于这一个“千湖之国”的印象不外乎是:美丽,祥和,银装素裹,高福利,健全发达的北欧社会等等字眼。然而,机缘巧合的是,我读到了小提琴大师,教育家奥尔(Leopold Auer,1845-1930)自传《我长长的生活》之中的文字,却感到了几分意外。他对芬兰的印象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美好:“不管是芬兰,还是它的邻国瑞典,自然环境都有着千篇一律的单调感,充满了忧愁。一望无际的冷杉与松木森林,流溢着泥水的小坑,灰暗,光秃秃的灌木丛林,时不时见到的小湖泊,从火山时代就盘踞在那里的巨大岩石,以及还未融化完全的,肮脏的积雪覆盖着道路两旁的沟渠。整体印象是:压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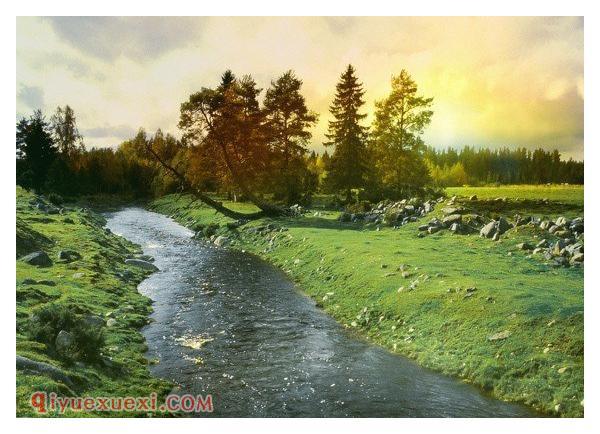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尤其在二十世纪初,西贝柳斯所在的芬兰是什么模样呢?恐怕文章应该以这样的疑问开场。从地图上一望即知,芬兰的欧洲诸国中地理位置最北面的一个。它的背面几乎延伸到了北冰洋。在芬兰中部,成千上万的湖泊和广袤的森林是两个标志性的景色。与整个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形类似,严寒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笼罩着这个国度,但有时海洋性气候所带来的暖流也会顾及到那儿郁郁葱葱的植被。在政治上,芬兰很早就自然而然地划分为了两个集团:“瑞典语派”和“芬兰语派”,但大部分受过教育的芬兰人都会说两种语言。追溯这个民族源头的工作还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其历史上受到过多民族,多人种的混合影响,我们暂且不表。但宗教方面,芬兰国内还是出奇的一致:九成以上的居民信仰路德教派。这也是芬兰社会的一大支柱之一。在芬兰文化的研究者眼中,芬兰当时的社会还离不开几个最重要的文化因素,那就是:创作《我们的国土》的伟大诗人J.L.隆涅贝格,他真实地记录了芬兰农村的故事和俄瑞战争给芬兰带来的苦难,西贝柳斯自年轻起就开始为隆涅贝格的诗作谱曲,断断续续维持了几十年;其次是隆涅贝格的后继者托佩利乌斯;还有积极宣传芬兰语,为之赢得合法地位的斯内尔曼;最后的,也是最关键是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芬兰人的长诗《卡勒瓦拉》,西贝柳斯的《库勒沃》交响曲正是对这部传奇作品的致敬,而其他极具芬兰本土色彩的交响诗的诞生也有赖于《卡勒瓦拉》所提供的,不竭的灵感源泉。然而,从另外一方面看,十九世纪的芬兰可谓是一个“文化的荒原”,W.A.威尔森在《西贝柳斯,卡勒瓦拉和卡勒瓦拉主义运动》中就这么提到:“太冷,太穷,我们可以毫不羞怯地说,那片国土完全不适合孕育出精神上缤纷的花朵。”芬兰在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一家艺术或博物馆的事实,说明了威尔森此言非虚。受气候、经济条件影响,固定的交响乐团、规则性的歌剧和芭蕾演出是一种奢望,单单在戏剧发展就受到了在语言上无法协调一致的恼人障碍。所以,在西贝柳斯这个名字出现之前,没有谁敢说芬兰能在音乐史上留下什么异乎寻常的痕迹,更罔论能猜测到一百年后的今天,“每两个大乐团的指挥家里就有一个是芬兰人”(《独立报》语)的惊人现状了。
历史上,芬兰本来与邻国丹麦、瑞典不乏友谊往来,但从中世纪开始,强势的瑞典就将芬兰的主权攫取了过来,之后断断续续的纠葛甚至战争一直没有中断过。可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始终是在东面虎视眈眈的俄国。在1808-1809年间的瑞俄战争中,瑞典战败,将原来在瑞典统治下的芬兰割让给了俄国,从此芬兰成为沙皇俄国的一个自治大公国。在十八、十九世纪,不少芬兰民众打小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观念:“俄国”这两个字意味着世世代代的冤家。一方面,俄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本来就高出人口少,城市少而乡村多的芬兰一头;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芬兰(芬兰缺乏近代工业化最重要的两个基本元素:铁与煤,只有较丰富的铜和泥炭。农业虽然是支柱,但是灌溉和耕种方式相对原始,效率不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俄国这个资源进口大国,也指望本国大量的木材等商品能在广阔的俄国市场上找到销路。民族独立的激情和上述的依赖性在19世纪成为了一对突出的矛盾。俄国方面,在1870至1890年间,它压制芬兰的尝试始终没有停止过。俄国一直希望芬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附庸国。1899年,所谓的“俄国化”几乎把芬兰的立法议会置于了俄国政府的监管之下,还强迫芬兰人学习俄语。民众顿时群情激愤,派遣代表团前往圣彼得堡公开请愿,西贝柳斯正是那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创作了著名的《芬兰颂》。那时的西贝柳斯,将近3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当芬兰几乎所有的文化媒体被封杀,被迫沉默的时候,他是用乐谱这种方式传达出最有力量的呼声的一位。1901年俄国得寸进尺,立法通过了芬兰的入伍人员必须去俄国军队服役。但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愈加加深了芬兰人心中的怒火。终于,1905年开始的独立运动在芬兰国内有星火蔓延之势,爱国青年首先去瑞典方面争取同情,但一直得不到实质性的援助,恪守中立原则的瑞典人袖手旁观。于是,芬兰舆论公开亲德,因为此时德国,是他们”敌人的敌人“,虽然芬兰人心里都清楚,德国本身就是军国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时局所迫,这个不怀好意的朋友是必须要交上的。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芬兰借助了这个时机,外加德国一定的帮助,压制住了国内由俄国力量资助的”赤色叛乱“,宣告了民族的独立。然而,为这次流血的独立运动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1918年前后,芬兰不仅丧失了俄国市场,货币更是贬值到了不及原先一成的地步。一切国内的经济秩序有待规范和振兴。也许是严酷的自然赋予了芬兰人顽强的意志和旺盛的自我恢复机能,从这一年起,芬兰的经济开始复苏了。首先是农业改革,将土地合理地划分给了农民,新农场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其次是耕种方法变得更加经济有效,小麦、马铃薯、奶酪等商品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此外,芬兰对木材资源的合理砍伐帮了这个国家大忙,没有了垄断者的存在,蒸蒸日上的木材交易与出口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铁和煤的缺乏。总之,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到三十年代末期的时间里,芬兰这个国家恢复到了比独立战争前更好的水平,西贝柳斯的创作繁荣期也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度过的。
可是,在西贝柳斯的晚年,芬兰再次陷入了不安分的骚动。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芬兰恪守中立的原则不但没有让它独善其身,反而接连遭到了被俄国入侵,被德国占领,最后还要承担作为轴心国一员,即理亏的战败者的悲剧性命运。几个回合的谈判与条约签订下来,在军事上处于弱势的芬兰永远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替罪羔羊,赔款割地,士气涣散。西贝柳斯此时的郁闷心情可以想象,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也只能接受时局,唯一可做的恐怕只有借酒消愁了。说到酒精,早在1919年6月起芬兰就颁布了禁酒法案,原因是酗酒、酒后犯罪和酒精中毒的事件频发。可是这个法案始终得不到民众实质性的承认,各种酒类仍然通过走私等渠道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人们手中。西贝柳斯的妻子阿伊诺曾对他沉迷于酒精深表忧虑,可是作为艺术的催化剂和对苦闷情绪的安慰手段,酒毕竟算得上一位对西贝柳斯不离不弃的朋友了。
第二部分 在芬兰那个时期的西贝柳斯
在芬兰,西贝柳斯一直起着文化座标的意义,芬兰本国人对他的尊敬从未减弱过。即便是在他作品产出量不大的晚年,芬兰政府依然慷慨地为西贝柳斯提供着可观的退休金,在荣誉上的奖励与认可更是不计其数,究其原因,除了在音乐上的客观造诣之外,西贝柳斯浓厚的“民族性”是一个最不可忽略的因素,芬兰官方乐于为这位百年一遇的作曲家贴上“芬兰出产”的标签,西贝柳斯也乐于这样接受。而他之前的韦格柳斯(Martin Wegelius)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作为赫尔辛基音乐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西贝柳斯的老师,韦格柳斯的作曲成就不可谓不高,但是其名声一直被局限在了北欧地区的小圈子里,在更早的十九世纪期间,芬兰这个偏远国度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过于冷淡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西贝柳斯的成功也有大环境作为恰当的催化剂。
一些传记认为,西贝柳斯的第一次作曲尝试是在1875年至1876年之间创作的《雨滴》,这部作品遵循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传统,采用了至简的小提琴和大提琴二重奏的形式,也有评论家觉得这部作品大约诞生于1880年后,直接起因是作曲家的哥哥克里斯蒂安开始演奏大提琴了。据称,此时西贝柳斯最喜爱的作曲家是海顿。在给佩尔叔叔(Uncle Pehr)的信中他写道:“在海顿的曲子里有一种深刻的、严肃的音调,它几乎是神圣的,让音乐在内部向我敞开。”渐渐地,西贝柳斯的三重奏作品中可以看到柴可夫斯基和格里格的影子。当他是赫尔辛基音乐学院学生的时候,获得了一笔奖金,去柏林研读一年。期间,听到了莫扎特的《唐璜》,并参与了瓦格纳歌剧的演出。汉斯·冯·彪罗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约阿希姆四重奏的演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打算去维也纳去维也纳投奔布鲁克纳或者勃拉姆斯的,但这个美妙的期望却落空了。最后,维也纳音乐学院的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uchs)接纳了他。接着,作曲家卡尔.歌德马克(Karl Goldmark)愿意从1890年开始做一些辅导,这大大激励了西贝柳斯在作曲事业上的热情。在维也纳期间,他听到了布鲁克纳第三交响曲(第三稿)的首演,深觉“布鲁克纳是在世的最伟大的作曲家”。1892年前后,西贝柳斯对瓦格纳的热情开始发芽,他决定效仿这位德国前辈。 《图翁内拉的天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谱写出来的。李斯特的《浮士德交响曲》同样感染了西贝柳斯,尤其是这种音诗般的体裁让他觉得异常亲切,“这和我走得最近,最近”。虽然《勒明盖宁》组曲(Lemminkäinen Suite)也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有了雏形,但西贝柳斯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部瓦格纳式的歌剧”。瓦格纳,或许是西贝柳斯提到的最后一位仰慕的作曲家的名字。如果没有归纳错误的话,青年西贝柳斯所受到的作曲前辈的影响就是这些了,虽说有点兼纳百家的气象,但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决定他未来道路的关键词。
其实,西贝柳斯的父母对与芬兰的独立运动并没有独特的情结,真正影响到西贝柳斯的民族观的,其实是西贝柳斯的朋友圈。1888年,赫尔辛基音乐学院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钢琴教师:菲洛齐奥.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很快与西贝柳斯形成了默契。一个由他们两人为主的音乐小团体在赫尔辛基的咖啡馆里悄然诞生了。这份友谊是珍贵的,而这个小团体也正是日后西贝柳斯朋友圈的雏形。晚些时候,西贝柳斯乐谱的首次出版了,曲目是为芬兰诗人隆涅贝格作品所谱写的小夜曲。这份喜悦是旁人所无法体会的,隆涅贝格文字中的“芬兰乡土味”隐隐地有股亲切的芬芳。恰恰也是在那个秋天,西贝柳斯的好友阿尔玛斯.耶尔纳菲尔特(Järnefelt )带他认识了一个亲戚,那就是他未来的妻子:阿伊诺。 阿伊诺那时17岁,她母亲是在圣彼得堡长大的,从小说的是俄语,但和阿伊诺的父亲同为芬兰语的支持者,可以说,当时他们一家正打算融入赫尔辛基的社会,这无形中让西贝柳斯去积极地去了解芬兰民族传统文化,这一切得归功于爱情的奇妙作用了。除此之外,阿尔玛斯.耶尔纳菲尔特还为西贝柳斯进入芬兰的媒体圈助了一臂之力,那时正是芬兰最重要的报纸《赫尔辛基日版》要即将诞生的日子,而阿尔玛斯恰恰是筹划者之一。正如开始提到的那样,西贝柳斯这个朋友圈的大体倾向是支持芬兰语和芬兰文化。要知道,在此之前,西贝柳斯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瑞典语(及文化)的拥护者,是朋友改变了他的想法,是芬兰国内涌动的新思潮赋予了他新的艺术生命。西贝柳斯开始严肃地端详起属于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自身的东西,芬兰,这个词语像一枚种子埋在了年轻人的心中。
《库勒沃》交响曲的成功是又一个重要因素。当指挥家卡雅努斯与西贝柳斯之间的友谊日渐紧密,两人频繁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的时候,西贝柳斯在昼夜不分地谱写《库勒沃》。这是一部为女高音、男声合唱、男中音、交响乐团而作的五乐章交响曲,取材于芬兰史诗《卡勒瓦拉》。谱写完毕之后,作曲家又义无反顾地接下了排演和组织的任务,每日奔忙不息,直至最后的首演到来。可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可这部新作,虽然有些芬兰人听到用芬兰语来歌咏《卡勒瓦拉》的时候兴奋异常,但也有观众表示能不理解它,尤其是那些支持瑞典语的批评家们更是持保留意见。卡雅努斯倒是倾尽了溢美之辞:“一颗新星升起了。”,他当时比西贝柳斯更权威的地位无形中成了《库勒沃》等作品的有力推手。也正是这部作品的成功(以及西贝柳斯准备去应聘音乐教师的允诺),促成了阿伊诺的父母同意了他们俩的婚事。1896年11月,他初次担任了赫尔辛基大学的音乐教师,试讲课上,他一语中的地提到了民族音乐的地位:“ 在巴赫那个年代,教堂音乐的力量正在消退。最终是民族性的,属于古老民歌的东西占据了上风。现在,我们也需要在民歌中发掘鲜活的声音资料,如果音乐离开了它在民间的根,那么必定是昙花一现的。”1899年,西贝柳斯搬到了克拉瓦(Kerava),目的是避开首府中五光十色的诱惑,专心投入到第一交响曲的创作中。同年时局大变,俄国沙皇签发了文件,从立法角度大大限制了芬兰民族的自由度,此举激发了西贝柳斯等人极大的愤慨,共同的爱国热情让“芬兰派”与“瑞典派”两批人扭成了一股绳。这就是著名的《芬兰颂》的创作背景。他写信给妻子:“我不知道新世纪会带给芬兰与芬兰人什么,但起码我们会有向往自由的意识。”1900年,他的第三个女儿夭折了,这却没有让悲痛的西贝柳斯放下笔。新谱写的第一交响曲同《芬兰颂》、《勒明盖宁》一道成为了观众们奔走相告的热门曲目,在十三个城市连演十九场的统计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勒明盖宁也是《卡勒瓦拉》中的一个人物,这支曲目的成功这让西贝柳斯吸纳芬兰民间素材的决心愈加坚定了。就此,从西贝柳斯创作的成熟期开始,“芬兰”这两个字在他的作曲中占到了头等重要的位置。西贝柳斯心里很清楚,自己最终要走的,并不是仿效他国的长处,是一条滥觞于芬兰民族本性,蹈厉在民族独立潮涌中的道路。
除了对民族的热爱,西贝柳斯对芬兰自然景观的倾心更是体现在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历史上就早有人评价说:“西贝柳斯的交响曲中,没有一个人出现,他写的都是自然。”前文已经提到,芬兰的地方风景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产生单调感,但西贝柳斯对它的爱不亚于任何一个土生土长的芬兰农民。无论是成片的蔚蓝色湖泊,波光粼粼的萨伊玛运河,数以万计的大小岛屿,常常笼罩在田野上方的迷雾,还是绵延数百英里的森林,以及它延伸到更远地带的黑色沼泽,乃至于森林中所传来的古怪吼叫和不绝于耳的回响,在他的耳朵中仿佛与啾啾的鸟鸣一样亲切。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本来在芬兰常常能遇见的,无生机的大片荒原在某些作家的笔下一定能成为鬼魂与幽灵的栖息地,浓雾升起,路面泥泞,谁也想不到西贝柳斯会将这样的景致取材到优美的交响曲中,他没有简单地把它处理成压抑与悲观的调子,而是赋予了勃勃的生机和野性的力量,让人联想起了远古时期的粗野舞蹈或者劳动号子,这样的音乐尊重自然,更赞颂安居于这片土地上的生命。
第三部分 三部不太被重视的交响曲
容许笔者借用有限的篇幅提一下西贝柳斯三部相对不被重视的交响曲:第三、第四与第六。首先,在古典气息比前几部更浓郁、而且较短的第三交响曲(Op.52,创作于1907年)中,西贝柳斯传递出了更正面和积极的信号,明亮而富于情调的主旋律压倒了黯淡不安的隐含情绪,其中的几个主题被认为与芬兰作家雅尔玛利.菲内斯(Jalmari Finnes)为清唱剧玛丽亚塔(未谱完)所作的歌词有关,而玛丽亚塔正是《卡勒瓦拉》长诗中一个近似圣母玛利亚的角色,她食用了一只浆果后怀孕,并生下了一名男孩,这种孕育新生命的基调贯穿了第三交响曲始末。第二乐章小行板在笔者看来是最迷人的一部分,主旋律据说是来自一首简单的芬兰民歌,格鲁吉亚钢琴家托拉泽(Alexander Toradze)认为这类似格鲁吉亚的民间调子。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惊诧于西贝柳斯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四次主题呈现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意味,这短短的七分钟兼具了忧郁、柔美和光明多种特质,实在是如歌如泣,催人泪下。关于这部交响曲的终曲,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画家帕尔维宁(Oscar Parviainen)在听了终曲的主题旋律之后,深受启发,为西贝柳斯创作了了一幅画像,它至今悬挂在了作曲家住所“阿伊诺拉”的墙上。
创作于四年之后的第四交响曲(Op.63)简练而富有诗意,但一度因其近似于室内乐的谱写手法和粗砺突兀的线条而被人认为是西贝柳斯全部交响曲的一名“异类”。它的主要乐思据说来自一次和好友耶尔纳菲尔特等人去科里山脉的旅行(Koli,在苏芬接壤的卡累利亚地峡处,是两国的天然界限),在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西贝柳斯提到,他就是想特意去听一听“风的叹息与暴风雨的怒吼”——这不正是第一乐章里时而飘逸得忘形,时而凝重得可怖的弦乐齐奏吗?卡累利亚地区独有的地貌特征(冰河、凹地、湖泊、沼泽)吸引着西贝柳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频频造访。所以我们今天能听到,在它的第二乐章里,牧羊人的长笛声和鸟儿的应和仿佛近在咫尺。在那次旅行的归途中,西贝柳斯发现了:复调手法具备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因为自然界的种种声响不仅仅是和声,更蕴含着多声部的奥秘,他从此开始希望用一个交响乐团来表现大自然,之前很少有人这么做过,因此在第四交响曲首演后,被听众们称之为“氛围太奇怪了”的不适应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另外,在这部交响曲中频频出现的三全音也成为了人们争论的话题,三全音在传统理论中一向被认为是“魔鬼音程”,诡异而且不稳定,它在这里加重了不安的气氛,加之让人猝不及防的强弱对比、近乎肉体在受苦中的挣扎感,第四交响曲被西贝柳斯研究者们冠以了“表现主义交响曲”的名号。
第六交响曲完成于1923年,相对而言也是被后人演奏得最少的一部作品,原因大约是与第五交响曲相比明显缺乏戏剧性,而更注重田园色彩。全曲并不复杂,多利安调式占据了核心地位,宏观上有点类似于由单主题激发的多次变奏,四个乐章因此唇齿相依。难点在于,在涵义稍显模糊的第二乐章中,速度问题让很多指挥家都难以把握。1951年,作曲家就向秘书抱怨:“他们过去把第二乐章指挥得让人昏昏欲睡,现在却又火急火燎似的。所以我几次改写了速度记号,从中快板,到小快板,最后定为小行板。”一些芬兰本土指挥家(如约拿斯.库克库能)认为人的年纪越大,对这部作品的接受度也就越高。作曲家本人在1943年说:“第六交响曲常常让我想起第一场大雪后的气味。”这部交响曲中所蕴含的平静与透明或许是作曲家从巅峰期走向暮年的最好写照。
正如没有人会混淆拉莫与巴赫,瓦格纳与德彪西一样,西贝柳斯的音乐与任何人都不同,芬兰的民族烙印一辨即知,从早期注重室内乐创作,到19世纪末受浓重的爱国情绪激励,再到20世纪初尝试用新手法发扬芬兰民族素材,最终在晚年归于平静、妥协与统一,西贝柳斯的一生经历了一个血气男儿的成长和成熟,也遍历了芬兰的苦难与复兴。但是,格里格和斯美塔纳那种鲜明的民族主义气息或许并不是西贝柳斯所要仿效的对象,在作曲时,他强调要用芬兰的本土元素(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歌等等);但等作品真正出来了之后,你会发觉那是一件浑然天成的东西,所包含的东西既不同于马勒“展现出一个世界”,也迥异于布鲁克纳的恢弘建筑感,西贝柳斯所叙述的只是一个人眼中的自然和眼中的世界,更确切地说,这是属于一个“自然见证者”的音乐。尽管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人对他不屑一顾,但事实却如西蒙.拉特尔所言:“西贝柳斯好似什么东西滴在你的皮肤上,立即就能穿过你的骨头燃烧起来。”无论听者是来自严寒的芬兰,还是来自他故乡千里之外的人,我想,这种感觉无一例外。 (nolix)

